编者按
我国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在2023年达到7.2%,人均卫生费用大幅提高,城乡家庭的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改善,我国医疗卫生科技与医院的医疗设备已接近全球先进水平。同时,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对我国由财政与医保筹集医疗保障与服务资金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冲击,基本医疗保障与服务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尚未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扭曲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医疗卫生机构与医务人员提高服务质量和节制医疗成本的内在激励机制尚未形成,过度医疗与医患矛盾的突出案例时有发生。为此,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关心中国医改的专家和研究人员,计划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以策略简报形式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我们第一期简报主要讨论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分配问题。 这一问题在很长时期内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的行为和费用成本。本期简报通过梳理国外医生的薪酬制度,对照我国的薪酬支付机制,提出改进薪酬分配制度的若干建议。
汤胜蓝,左学金, 葛延风
1中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背景、演变及其问题
绩效工资为主的公立医院薪酬体系是改革开放后提升医疗工作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并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医生薪酬制度为“供给制”和“工资分制”并存。1956年开始实行医务人员职务等级工资制,主要根据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劳动技能等因素将工资分为21个等级。然而,级别间差距较小,无法准确反映技术高低,影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1]。改革开放后,我国颁布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政府放宽政策,放权让利[2],医疗单位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部分收入以奖金形式分配给职工个人,薪酬中绩效部分逐渐成为收入主体并延续至今。2006年中国公立医院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3],医务人员薪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其中,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分为专业技术、管理、工勤技能等岗位,薪级工资设置不同等级。绩效工资一般可细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津贴补贴主要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卫生防疫津贴、特殊岗位津贴补贴等[1]。薪酬水平方面,根据《2021年度中国医院薪酬调研报告》,2020年中国公立医院医生年平均薪酬约20.2万元,是社平工资的2.1倍[1]。薪酬结构方面,全国公立医院固定薪酬所占比例约为41%,一线城市固定薪酬比例仅为29%左右,较非一线城市低15个百分点;三级医院固定薪酬比例约为36%,较二级医院低8个百分点。薪酬差异方面,不同区域的薪酬差异较大,2020年上海市医院医生平均薪酬最高,约为35万元,最低的城市仅为5万元左右;不同级别医院薪酬差距较大,三级公立医院年平均薪酬约为二级的1.9倍;不同职称的医生薪酬也存在差异,正高职称薪酬约为初级职称的1.8倍(见图1、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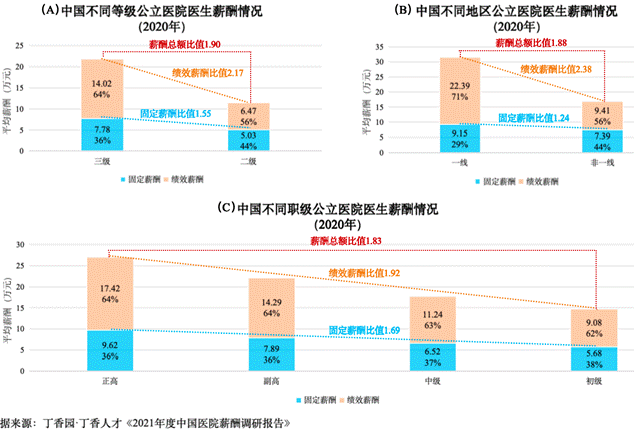
图1 中国公立医院年均现金薪酬水平(万元)情况(2020年)

图2 中国不同城市医院平均年度薪酬统计(2020年)
当前公立医院的薪酬制度存在结构失调、绩效考核以医疗为中心、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影响医疗服务合理性。一是薪酬结构失调,固定薪酬占比较低,医生收入主要取决于绩效,其行为易受绩效指标影响;二是绩效考核以医疗服务为中心,关注服务类型、数量、费用,以及对所在医院净收益贡献等,激励医生追求更多服务与更高费用。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分解住院等问题均与此有关;三是区域、机构、专业间分配不均衡,薪酬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如2020年三级公立医院年均固定薪酬约为7.8万元,比二级医院高近55%,绩效薪酬的差距则更为显著。客观上,这可能导致医生的工作或对健康改善的贡献类似,但由于身处不同区域、不同机构、不同科室,收入差距大,影响公平性。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际上典型国家医院薪酬制度的设计要点,尤其关注薪酬结构、薪酬水平、薪酬决定因素等,为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2中高收入国家医院薪酬制度经验总结
本研究选择英国、瑞典、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巴西等8个有稳定医生薪酬体系的国家,以医疗机构雇佣医生(后简称“受聘医生”)为重点分析对象,梳理薪酬制度基本理论、薪酬模式、薪酬结构、薪酬水平、薪酬确定方式和决定因素及其对于服务供给的影响等。
2.1 薪酬理论及薪酬形成机制
医生薪酬水平通常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主要源自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和医生的高“生产成本”。医疗服务以“健康”作为最终产出,“健康”是人们生活的基石,是决定人类福祉/效用的关键因素,这决定了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同时,医生在执业前需要经历漫长的教育和培训周期(包括5年院校培养、1-3年住院医师培训、2-5年专科医师培训,全程周期大多在10-13年左右[5]),就职后需参与继续教育等,保持知识更新。相较于其他行业4-7年的培养周期,医生就职年龄较晚,前期投入高,故医生的“生产成本”更高。这种服务的高价值及服务提供者的高成本,需要更高的工作薪酬。因此,全球层面,医生高薪酬是不同国家的普遍做法[6]。
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要求,决定同类别医生薪酬的相对同质性。一般市场中,劳动力价格(薪酬)受价值、成本及劳动力供需关系影响。但无论在城市还是偏远地区,都要求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这意味着医生的配置以及医疗服务的提供都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同时,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在服务数量、质量上应该接近,这种服务的同质化要求,也决定了医生能力的同质化。从这个角度,同类别医生薪酬差异应该较小,不同科室间医生薪酬可以略有差异。日本的医生薪酬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其薪酬更多基于资历,执业地点对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7]。
医生薪酬应维持在稳定水平,并随社会经济发展稳中有升。医疗服务的价值及医生的“生产成本”都比较稳定,价值与成本决定了价格。从这个角度,医生的薪酬也应当较为稳定,这也是保证医疗服务公平可及的基础之一。公立医院薪酬稳定的基础是机构拥有稳定的筹资。当前医院收入主要来自政府投入、医保补偿和个人支付以及其他收入。其中,财政投入与医保与个人支付中的医疗服务部分(非药品、耗材等)是医院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如何保持医院筹资的稳定性,尤其是财政投入和医疗服务收入部分的相对稳定,是保持医生薪酬相对稳定的前提。此外,医生薪酬水平和增速应与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相关联。在我国,公立医院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同机构间收入差异过大,筹资不稳定,进而导致医生薪酬不稳定且差异大的局面,使“两个允许”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挑战。
2.2 薪酬模式和薪酬结构
国际上的医生薪酬主要分为三大类:以时间为基础的工资制(Salary)、以服务为基础的项目支付制(Fee for service, FFS)、以人口为基础的按人头支付制(Capitation,CAP)。其中以时间、人口为基础的薪酬,一般会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工作时间及服务人口,而后采取固定薪酬方式。以服务为基础的项目支付制则是浮动薪酬方式。此外,按绩效支付(Pay for performance,P4P)、混合支付(Mixed payment)等也成为近些年的重要薪酬模式改革方向。
国际经验显示,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以固定薪酬为主;私立医院医生薪酬多采用按服务项目支付,其水平取决于服务提供[8]。公立医院医生的医生薪酬,大多由基础工资、津贴或奖金等经济性薪酬以及带薪休假等非经济型薪酬组成。英国受雇于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医生薪酬以固定工资为主,自由执业的全科医生中75%的收入为按人头付费收入(固定),另有25%为按绩效收入;且自由执业者转为受雇工资制医生,绩效部分减少的趋势日益明显[9];此外,英国公立医院医生享受免费社会医疗和保险福利,拥有灵活上班时间、产假及育儿假、带薪休假、带薪病假等非经济性薪酬[10]。澳大利亚公立医疗机构医生薪酬主要由工资和福利构成,全科医生的固定工资是收入主要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直接拨款[11]。瑞典、新加坡、泰国、巴西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生薪酬均由占比较大的基本工资和占比较小的奖金、津贴等构成,奖金主要由绩效决定,津贴包括加班津贴、艰苦地区津贴、专科津贴等[12-14]。
2.3 薪酬水平
不同国家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故本文采用医生收入与国家全行业平均收入(后简称“社平工资”)的比值衡量医生的相对收入。上述8国医生收入均显著高于同时期社平工资,约为社平收入的1.5-4倍,部分国家专科医生薪酬高于全科医生。根据2023年OECD统计数据,英国受薪全科医生收入约为社平工资1.8倍,受薪专科医生约为3.3倍。瑞典受薪全科医生收入约为社平工资的2.3倍,受薪专科医生为2.2倍[15]。加拿大医生收入约为社平工资的3倍[10]。新加坡全科医生薪酬约为社平工资的2.3倍,专科医生薪酬约为3.6倍,同时新加坡卫生部明确在2023-2025年上调医疗人员薪资[16]。泰国的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生薪资标准高于一般公务员(大约为1.4倍)[17]。巴西医生收入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4倍[18]。
2.4 薪酬确定方式和决定因素
医生薪酬的形成是政府、行业协会、医院等多方博弈的过程。为确保医疗服务的稳定供给和区域公平,政府一般会参与薪酬体系设计,如设定最低薪酬标准、发布薪酬指导线、推进薪酬体系改革等。英国医护人员的薪酬框架由政府通过卫生部与医疗委员会协商制定,对各级别医护人员薪酬水平及结构都有较详细的规定,医护人员工资根据薪级由政府财政统一拨付[19]。巴西公立医院任职医生的薪资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故其水平受政府预算影响较大[20]。除政府外,工会或医师协会代表医生群体与政府或医疗支付方进行谈判,制定医生薪酬标准、服务价格等[21],如荷兰国家全科医师协会(LHV)、英国医学会(BMA)、瑞典医学协会(SMA)等。
各国在医生薪酬梯度设置和分配中,主要考虑医生的经验、职位、职称等因素,此外,有时也会考虑服务人口、执业地区特征。如英国在设置医生固定薪资时,还会考虑医生从业地区的人口数、年龄结构、地区偏远程度[19]。澳大利亚的医疗补助(Medicare Benefit)和患者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是全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22],其中,医疗补助部分来自政府医疗看护补贴计划(MSAC)的直接拨款,与其签约服务量及服务效果挂钩[11],同时还根据地区偏远程度和在该地区的从医年限,为医生设置了不同的补助标准,并因此设计了劳动者激励计划(WIP)、实践激励计划(PIP)等激励项目[23]。
2.5 薪酬制度对于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薪酬制度作为影响医生行为的重要激励机制,对医疗服务数量、费用、质量、效率等医疗服务供给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情况与特定薪酬制度的支付方式密切相关,按服务项目支付、按绩效支付下,医生对于自身所得薪酬的可控性强,固定薪酬下可控性弱,按人头付费下带来的结果更接近于固定薪酬。澳大利亚学者对比国家公立医院的工资制与私立医院的按项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选择患者的经济激励,按服务付费制则导致医生显著偏向治疗短期住院患者[24]。按绩效支付方式、混合支付的影响尚不明确,可能与不同的绩效激励方式或不同的支付方式占比有关。挪威学者评估公共牙科服务中混合薪酬制度(固定工资+按人头付费)对患者选择效应和质量(龋齿治疗水平)的影响,证明该制度能在不损害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降低患者的平均治疗成本[25];英国学者对英国初级卫生保健绩效支付计划(QOF)评估显示,绩效支付计划对血压监测控制及治疗强度等无显著影响[26];加拿大的混合薪酬制度(固定工资+绩效)导致服务量降低,住院时间延长,住院成本增加,但未能转化为健康收益(再入院率未降),提示服务效率与质量间存在权衡[27]。可见,工资制、项目支付制、人头支付制等单一的薪酬支付方式难以实现医疗服务供给行为及结果的最优解,合理的“工资+绩效”混合支付模式,有望平衡质量、效率和成本控制目标。
3启示与建议
3.1 优化薪酬结构,强化固定收入为主的混合薪酬制,弱化经济激励导向
当前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结构中,绩效工资占比过高,医生易出现追求绩效指标而导致过度医疗等问题。国际经验表明,以固定薪酬为主的薪酬模式(如英国、瑞典)更有利于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公益性。建议逐步提高固定薪酬占比至60%-80%,构建“基础工资+有限绩效”或“基本工资+小比例绩效奖金”的结构,降低绩效奖金与业务收入的直接挂钩强度。同时,建立薪酬资金优先分配机制,确保医疗服务收入用于人员奖励时,优先补充固定薪酬部分,从制度设计上避免绩效驱动的短期逐利行为。
3.2 构建差异化补偿机制,平衡区域与岗位薪酬差距
我国医生薪酬呈现显著的区域与岗位失衡,不同地区医生年均薪酬5-35万元不等,儿科、全科等岗位收入偏低,这是西部地区全科医生离职意愿率超33%的重要原因[28]。国际上,澳大利亚对极偏远地区医生首年最高补贴2.5万澳元,实行服务年限累进奖励[29];英国根据执业地区人口结构、年龄分布制定差异化薪资标准[19]。建议建立“基础薪酬+区域补贴+岗位系数”的三维补偿体系:按经济水平和医疗资源紧缺度设置3-5级区域补贴(如西部偏远地区可设置20%-30%基本工资的补贴、农村地区可依据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设置偏远地区津贴和艰苦津贴),服务满5年补贴翻倍;对儿科、急诊等岗位设置1.2-1.5倍的岗位系数;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的薪酬资金,缩小不同层级医院的收入差距。
3.3 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商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体系
当前我国医院薪酬标准由各机构自主制定,缺乏统一框架导致同职称医生收入差距可达2倍以上。英国卫生部与英国医学会协商制定全国统一的薪酬框架[19],荷兰政府、保险公司、全科医师协会三方谈判确定薪酬标准[21],以实现薪酬体系的规范化。建议探索构建由卫健部门、医保局、人社部、医师协会、医院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薪酬委员会,形成相对统一的薪酬框架,每2年调整一次薪酬基准线并向社会公开。绩效考核方面,可考虑将经济指标权重从当前的60%以上降至30%以下,增加患者满意度、临床结局(如并发症率)、健康管理成效等质量指标及权重。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考核与评价。
3.4 加强财政保障,推动长期职业激励
公立医院医生薪酬稳定的前提是机构筹资的稳定,这需要改变原有的公立医院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化运营模式。薪酬改革中,需要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同时考虑调整价格体系,以增加医院的医疗服务类收入。加拿大联邦与省级政府共同承担医生薪酬资金,澳大利亚政府医疗看护补贴计划为医疗补助提供直接拨款[22],以保障薪酬政策的落地。建议提高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水平,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置一定增幅要求(如8%);推进医疗服务收费改革,增加医院收入中医疗服务收入比例;探索构建多元化职业激励体系,将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先、学术交流资助等纳入薪酬,形成“经济保障+职业发展”的双重激励。
附表 各国薪酬制度特点整理
| 国家 | 薪酬模式 | 薪酬结构 | 薪酬水平(与社平工资比值、2011-2021薪酬年均增长率)及资金来源 | 薪酬确定方式 | 薪酬决定因素 |
| 英国[9,15,30] | NHS雇佣医生:固定薪资为主;自由职业者:按人头支付为主 | 固定为主,占比>70% | 机构受薪医生薪酬:全科1.8倍/专科3.3倍;自雇医生薪酬:3.4倍 增长率(受薪):全科-0.3%/专科-0.7% 资金来源:政府预算 | 固定薪酬部分由政府制定;英国医学会(BMA)参与谈判,影响绩效指标等 | 固定薪资:年资、级别、从业地特征(人口数、年龄结构、地区偏远程度等) |
| 瑞典[14,15,17,31-33] | 公立医院医生:固定薪资为主;私立医院医生:按服务量支付为主 | 固定为主,占比>80% | 机构受薪医生薪酬:全科2.3倍/专科2.2倍 增长率(受薪):全科0.3%/专科0.1% 资金来源:政府预算 | 劳资谈判;瑞典医学协会(SMA)与医疗机构进行年度工资审查 | / |
| 荷兰[15,21] | 机构雇佣医生:固定薪资为主 | 固定为主 | 机构受薪医生薪酬:全科2.2倍/专科3.2倍;自雇医生/医生薪酬:全科2.5倍/专科3.3倍 增长率(受薪):全科0.8%/专科-0.6% | 政府设定服务价格范围;政府、保险公司、荷兰国家全科医师协会(LHV)协商价格制定 | / |
| 加拿大[10,15,34-36] | 4种薪酬模式混合 | 依据不同薪酬模式,固定薪酬占比程度有较大差别 | 医生薪酬:3倍;自雇医生薪酬:全科2.7倍/专科4.2倍 增长率(自雇):全科0.3%/专科-0.1% | 劳资谈判 | 固定薪资:年资、级别、从业地特征等;绩效薪资:工作效益、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完成工作量 |
| 澳大利亚[11,15,37] | 混合支付机制 | 全科医生以固定为主 | 自雇医生薪酬:全科1.7倍/专科3.8倍 增长率(自雇):全科0.4%/专科-0.7% 薪资来源:政府预算、个人自付 | / | 除个人因素,考虑从业地区,偏远地区补助 |
| 新加坡[16] | 工资制 | 固定为主,占比>70% | 医生薪酬:全科2.3倍/专科3.6倍 | 新加坡保健集团内部实行统一薪酬制度 | 工资:年资、级别、职位等;绩效:患者满意度、临床结局、机构目标 |
| 泰国[12,38] | 公立机构:工资;私立机构:保障+绩效 | 固定为主 | 医生薪酬略高于一般公务员:约1.4倍 | / | / |
| 巴西[13,18,39] | 工资制 | 固定为主 | 医生薪酬:3-4倍 | 政府决定 | 地区补贴 |
[1] 社平工资是指《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7397元;与社平工资的比值=全国公立医生平均薪酬/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